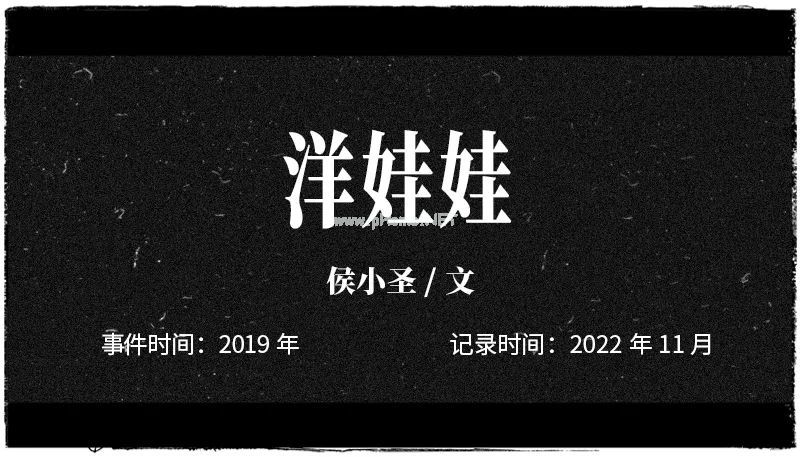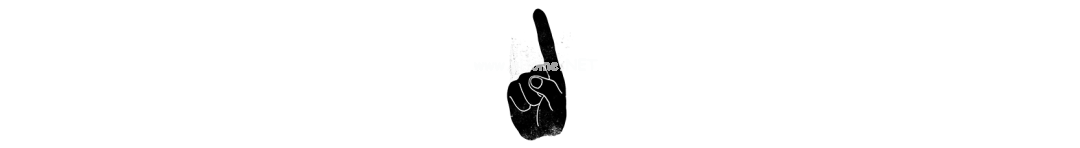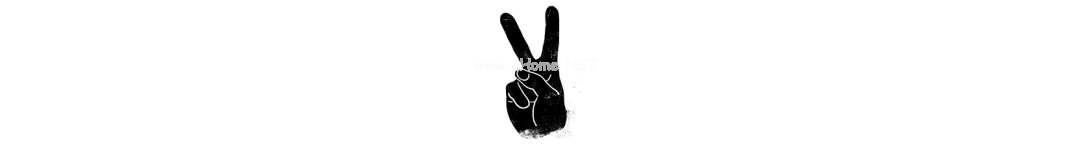#医生日记#是程明帅小儿推拿整理的文摘类栏目
站在医生的视角讲述生活百态
有人说律师和医生是最能接触人性本身的职业
希望这些故事带给大家思考和启发

大家好,今天的故事有些特别,或许很多人一辈子也碰不上。
但故事里的现象可能我们每天都在发生,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这种找不到问题症结的困惑和狂躁。
当问题发生了,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针对问题本身,但很少去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。
孩子的问题找不到根源,孩子就莫名其妙的哭闹,乱发脾气;大人找不到问题的根源,总是有种无名怒火,本来没事也要找茬。
找到了问题背后的真凶,可能你都不需要解决,一下子自己就释怀了。
遇到问题多想一想,想想为什么会这样?或许很多问题就不会演变到不可收拾了。一起来看今天的医生日记吧:
它来自我的朋友,社工侯小圣,她之前遇到一个女孩,像个活体洋娃娃。
女孩不允许自己说话、也不排泄、甚至连眼睛都不眨,永远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。
随着侯小圣调查越来越深,她逐渐发现,这女孩的经历里,能看到有很多家庭的影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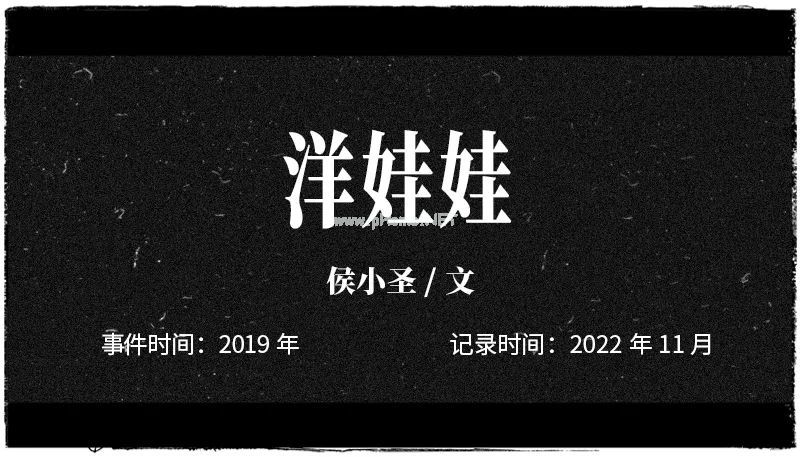
夜视的莹莹绿光下,平日里奇形怪状的精神病患者们都已经睡了,只有一个小女孩还坐在床上,一动不动。
实际上,就算我现在钻到监控里和她对视,她都不会眨一下眼睛。
按照主治医生的说法,她就像一个有心跳的洋娃娃,不吃饭、不喝水,甚至不排泄、不眨眼睛。
我隔着摄像头盯了她一整天,就在这场对峙进行到后半夜时,监控里的洋娃娃终于动了。
她悄无声息地舒展四肢,滑下了床,踮着脚轻轻地溜进了洗手间。
没有灯亮,没有冲水的声音,不一会她就出来了,站在门口,突然抬头看了一眼斜上方。
我好像被一道目光隔着监视器盯住,莫名地汗毛倒竖起来。
她会选那种不用撕开包装袋甚至不用咀嚼的东西,进食的全程比老鼠还安静,吃完以后又静悄悄地溜回床上。
这个小姑娘根本不是不会动,就是有意让自己“静止”。只要身边有人,她就会进入静止状态,直到所有人都睡着,才会出来吃喝活动,不发出一点声音。
更让我们困惑的是,兰琦的这些异常行为,住进医院不久后就会消失,变得像正常女孩一样,会跑会跳,对自己之前的情况没有任何记忆。
但她一旦“康复”回家,没多久,又会恢复成洋娃娃的形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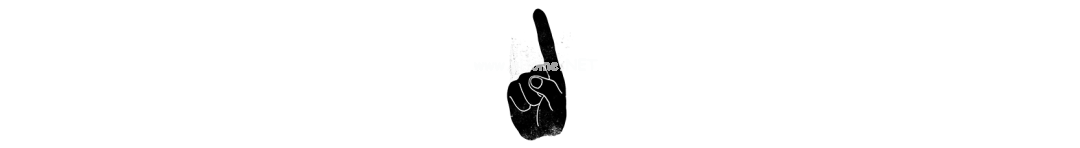
在澳洲做司法社工的第二年,我已经学会一个知识:孩子会替整个家庭生病。
当一个家庭里出现暴力、冷漠,或者是家里的大人存在种种心理问题,孩子作为家庭里最脆弱的一个,往往最容易成为收集恶意的盒子。
尤其兰琦这种情况,往往就需要社工上门家访,确保她没有在家门背后被家暴、囚禁、冷暴力什么的。
兰琦的资料上只登记了一个亲属,是她的哥哥兰瑞,21岁。这也是兰琦几次入院出院接送她的人。
我给兰瑞打了个电话提出要去家访,对方答应得非常痛快。
我找到他家的时候,这个大男孩站在门口迎接我,笑着带我走进了他家。
就在门关上的那一刹,我一抬头,猛地和“自己”打了个照面。
我吓了一跳,接着才反应过来那是一面一人多高的巨大镜子,就放在门口。镜子底座的空隙处还放着几个小蜡烛,都有燃烧过的痕迹。
我脑子里一下闪过一百个都市传说。上一次同事也在家访时见过这么大的镜子,接着他就被那个信邪教的房主从后脑勺来了一下子,人直接住院了。
屋子里安静得吓人,兰瑞站在我旁边不说话,兰琦也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,脸色苍白。
整个家里只有这一对兄妹,没有他们的父母,也没有本该从窗户传进来的邻里熙熙攘攘的声音。
这间房子离人群很远,称得上郊区了。没人能及时赶到这里帮我。
我强装镇定地跟兰瑞自我介绍,试图问他几个简单的问题:
一问一答,自然极了。两句话说完后,屋里又陷入了可怕的寂静。
我去房间里看兰琦,她端坐在自己的小沙发上,背后是白得晃眼的墙壁。上一次出院时她还是会蹦会跳的,现在看来,已经又回到洋娃娃状态了。
我敲了敲门,不出所料的,她毫无反应。但跟在我身后的兰瑞不知道为什么,晃了晃头,往后退了几步。
我脑子里的一堆备案全都被自己的心跳声掩盖了,只想着怎么逃跑。
一直到关上兰家的大门,确定兰瑞没有送出来,我才下意识地舒了口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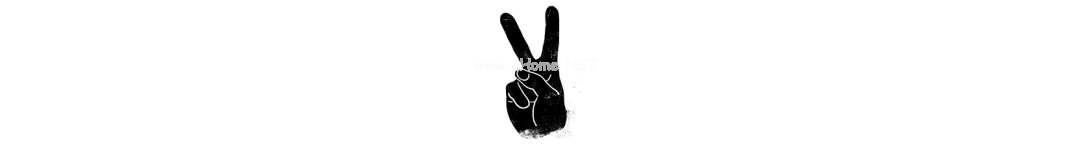
在那扇门背后,所有我习以为常的环境背景音都不存在,包括钟表的滴答,电脑主机发出的轻微的嗡嗡声,甚至水管里水流动的声音,人的呼吸声。
大部分人都以为嘈杂才会烦人,实际上过于寂静也会使人感到巨大的心理压力,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那么紧张。
仔细一想,兰瑞本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,他看起来就像个有些腼腆的大男孩。
在整个家访过程中,他一会站起来问我要不要吃东西,一会儿又去洗洗手,中途甚至跑到后院去烘干机里拿了一次衣服。
我还记得他从那堆衣服里分出一堆小袜子,一双双地叠好,显然都是妹妹兰琦的。
母亲声称女儿有残疾,孩子也确实不会走路。但因为没查到这家人申请残疾补助的资料,我还是有点疑心,叫来了警察。
最终,我们发现女孩根本没生病,她的残疾只是因为母亲“觉得她有病”,禁止她出门、禁止她起床,最终导致孩子肌肉萎缩,“不会走路”。
当时那个母亲也表现得非常关心女儿,整个家里全是防磕碰的软垫,但这恰恰是她控制女儿、毁了女儿的方式。
兰家那么安静,显然是安装了特别的隔音装置,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?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?
而且和那个控制狂母亲一样,兰瑞也没有给生病的妹妹申请补助,这很罕见。
我再去查了一次兰瑞兰琦的资料,发现他们是从其他州搬来维州的,他们的父母不在这里。
这就意味着我要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、弄明白这对兄妹的过去,需要花很长时间。
距离她上一次出院没过去多久,人刚回家,又变成了洋娃娃。如果兰家真的有问题,她还会遇到什么?
我挑了个同事们一起出外勤的日子,跟他们打好招呼,万一我需要什么帮助他们确保能赶到。
这一次,我极力不看那面奇怪的镜子,而是尽可能自然地观察些其他的地方。
如我所料,窗玻璃是加厚的,地上铺着厚地毯,门锁加了隔音塞。
就连所有家具的颜色都是白色灰色的,显得特别“安静”。
兰瑞还是像上一次一样,腼腆又拘谨。他想给我找个杯子喝水,站在桌子前就犹豫了起来。
兰瑞点头后,我就在家里简单走了一圈。果然,这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两人份,小到碗筷拖鞋,大到桌椅柜子。
这意味着什么呢?哥哥极端恐惧声音,赶走其他人的同时,逼妹妹变成一个洋娃娃?

我在小屋里转了一圈,从兰琦的屋子里走出来时,兰瑞就像等在手术室外的家属一样,焦急地问我,妹妹现在情况如何,是不是又该住院了?
我说“还不确定”,接着想起自己的猜测,决定试探他一下。
我故意抬高音量问他,你觉不觉得这里太安静了?我能放点音乐吗?
兰瑞犹豫了很久,也没说行不行,但他的肢体语言已经泄露出一些痕迹——拳头捏紧,身子贴向椅背。
看起来,我还没开始放音乐,只是抬高了嗓门,他就开始想尽量离我远点了。
我又把音量降低,兰瑞明显放松了不少,甚至语气讨好地说,他觉得我比那些医生亲切多了。
我径直打断他,开口问道:“你很怕高分贝的声音吗?”
我明显看见兰瑞的肩膀抖了一下,但他坚决回答说没有。
两个问题节奏很快,我想如果他心里有鬼,如果他害怕声音的事情和妹妹有关,一定会表现出一些异常。
但这时候兰瑞又显得非常老实,他说买镜子就是因为妹妹兰琦想染发。
他说,妹妹喜欢把头发染成棕色的,他们没钱去理发店,所以从二手网站买了这个镜子,专门用来染头发的。
怕我不信,他又去找染发膏给我看,还有专门的梳子和护发精油,甚至还有一个大的罩袍,虽然上面还有一些斑驳的染发剂痕迹,但能看出经常用,被仔细洗过又叠好。
染头发那么麻烦,可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满足妹妹的小愿望。
我也看到,兰琦虽然生病,但近看皮肤、头发都很好,衣服也干净整洁,连指甲都被整齐修剪过,是被精心照料的表现。
就连附近的邻居都记得这个好哥哥,记得兰瑞曾经带着妹妹挨家挨户拜访,说两人刚搬来,妹妹还没有上学,平时一个人在家,希望大家多多关照。
那时候,兰琦虽然有点害羞,总往哥哥身后躲,但并没有一点“洋娃娃”的迹象。
还有邻居说,之前有次兰瑞来拜托他们第二天早上不要除草,因为妹妹想在院子里“露营”体验一下,他怕妹妹早上被吵醒。
邻居们看到那天傍晚小女孩在院子里兴奋地跑来跑去,也看到第二天兰瑞一直等到妹妹睡醒回房间,才出门替邻居们补上除草的工作。
我的猜测似乎只对了一半,兰瑞是有点害怕声音,可是这和兰琦没关系,他对妹妹很好,没有什么控制行为。
我决定最后测试一次,看看兰瑞害怕声音这个特质究竟会严重到什么地步。
刚见面我就发现他戴了一只耳机,大概他出门都会戴着耳机,只是为了要听我说话,才不得不空出了一只耳朵。
果然在医院大厅刚坐了一会儿,他就受不了了,提出要出去呆一会儿。
我把他带到一片树荫下面,但紧接着就又打开了手机外放,假装打字聊天,键盘不断发出哒哒的声音。
椅子突然被掀翻了,这个一直保持着礼貌温柔的男孩像变了一个人一样,冲我大喊:安静!马上安静!
我们在大楼的背面,周围空无一人,兰瑞弯着腰,双手支在膝盖上,眼睛发红地瞪着我,我收起手机走近他。
不论兰瑞平时是一个怎样的三好哥哥,噪音会让他发疯,会让他表现出暴力倾向。
这一定就是他11岁的妹妹兰琦把自己“静音”的原因。

就在这时,我联系兰瑞和兰琦父母的申请终于收到了回音。
但我收到的不是一串电话号码或一个地址,而是一份判决。
在那份判决里,记载了兰瑞遭遇的近二十年的家庭虐待。
从兰瑞刚出生开始,他的父母就酗酒,喝了酒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他。
这对夫妻在法庭上供述,他们这么做是因为“有意思”。
案子的社工在边上注释:“指‘小孩没有能力反抗’有意思”。
男人最喜欢的施暴方式,是把兰瑞拎起来随机往旁边的墙上丢,力气越大,他撞在墙上越大声,他就会越满意。
兰瑞告诉社工,小时候有一次他被丢出去,正好掉进了妈妈怀里。
那怀抱的温暖使兰瑞误以为自己得到了保护,但妈妈只是哈哈大笑,然后用更大的力气把他摔到墙上。
当时她用乐不可支的语气和丈夫调侃着兰瑞:“他居然觉得我会救他?”
但他也记得有一次,他被折磨到呕吐后,母亲破天荒地关心了他,摸着他的头问他怎么样。
他害怕地挣脱了她的手,于是女人再一次陷入愤怒,把他面前所有的东西都砸了。
兰瑞后来想,也许挨打是他的错,是他没有抓住那次机会。
随着他慢慢长大,暴力越来越日常化。每天下班回家后,两个人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拎起来往墙上丢。
兰瑞一开始会哭,父亲于是打他打得更厉害,说他不像个男子汉。
每当俩人窃窃私语一阵,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,兰瑞就知道自己又要遭殃了。
手掌打在后背和屁股的声音,自己的身体撞到墙壁的声音,水杯被砸碎的声音,打开酒瓶的声音,包括家门开关的声音。
这对夫妻从来不让兰瑞出门,不让他上学,也不让他见任何人。如果没有兰琦,兰瑞可能真的要到被打死才会被发现。
也许是因为突然爆发的雌激素,也许是因为怀孕时不好再“照顾”兰瑞,兰瑞被送到了一个类似教会开办的福利机构上课。
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外界,这里没人会突然打他,还有免费的午饭和晚饭,并且不是酒。
兰瑞的父母会逼他喝酒,从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开始,他们就会掰开他的嘴,把烈酒混合在一起灌进他的嘴巴,然后看他呕吐。
相比之下,学校简直太好了,兰瑞经常清晨趁父母没醒就溜去学校,呆到所有人全离开,再依依不舍地回家。
那就是妹妹兰琦,她出生了,小小一个,缩在毯子里,一双眼睛叽里咕噜转来转去。
兰瑞说,那一刻他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——要是把她扔到墙上会怎么样?

他手忙脚乱地把兰琦抱起来,还不知道要怎么办,结果兰琦盯着他,突然不哭了。
小小的男孩举着小小的婴儿,就那么在婴儿床边站了一下午。
从小到大,兰瑞习惯了恐惧,但这是他第一次替别人恐惧。
他第一次看到一个这样脆弱的小东西,像花草,像自己,像自己的心。
父母曾再三叮嘱他,如果敢把家里的事往外说,他也不用再上学了。
于是他无师自通地编造了一个谎言,跟老师说是因为爸妈平时都不在家,兰琦太小了,他不能让兰琦自己在家,就抱来了。
兰瑞急得拿身子堵住教室门,说是父母让他照顾兰琦的,但老师还是坚持放学之后要去他家看看。
那天,兰瑞的妈妈在家,她在门口亲切礼貌地和老师打了招呼,解释说兰琦离不开哥哥,她才让他们一起上学的,以后不会了。
妈妈让兰瑞在门外站着,从他怀里抢过兰琦,转身要进门。
那天,兰瑞第一次发了疯,他死死咬住妈妈的手,把妹妹抢到自己怀里。
妈妈怕邻居听见动静出来看到,把他们两个都推进了家门。
兰琦在一片混乱中嚎啕大哭,兰瑞抱着她钻进自己的房间,躲到了床底下。
他知道妈妈没法拖开这张床抓住他,直到爸爸回来之前,他都是安全的。
在黑暗里他贴着墙壁,兰琦被他小心地放在胸口,很快也不哭了。
兰瑞听见,除了自己快速的心跳之外,还有另一个人的呼吸和心跳,是平静的,安稳的,对他没有恶意的。
这在以后的十年里,成为支撑他人生的最重要的片段之一。

那天他被晚上回来的爸爸打得很惨,而他只是一言不发地盯着兰琦的方向,一直想象妹妹安稳地躺在他胸口的那十几分钟,用来忍受身体的痛楚。
打到最后,他依旧坚持着靠在兰琦床边,第一次和父母谈判。
他那个时候太小了,只知道威胁,手上的伤口蜿蜒,因为攥拳用力过猛而鲜血淋漓。
他和父母说:“你们不能打她,不然我会告诉老师和邻居,我知道你怕他们知道。”
他们开始辩解,说只是和他闹着玩,说爸爸妈妈压力太大,又威胁他,你现在还必须住在我们的房子里,你就要听我们的。
而兰瑞只是反复重复,你们不能打妹妹,不然我一定会告诉所有人。

兰瑞替妹妹扛下了所有的暴力,他和父母达成了一个无声的默契,只要他们只打他,这一切就不会被捅出去。
这一切持续到了他18岁那年,老师建议兰瑞去考个学校,他说这花不了什么钱,他自己就能去,不需要父母的支持。
兰瑞反复确认老师的说法后,第一次发现,原来他是可以逃跑的。
那时候兰琦已经七岁了,也许因为在学校里长大,她令人意外的聪明懂事。
而父母的暴力也已经越来越少了,也许是因为长期酗酒,他们打不动了,喝醉酒只会砸东西、呕吐,不停地咒骂无意义的话,然后睡着。
因为他们只是打砸东西,这对兄妹不用再在房间里四处躲藏,他们发明了新的游戏。
每当父母动粗的时候,两个人就会躲进房间里,互相捂住对方的耳朵,看谁捂得最严实。
他不敢想象,如果把妹妹一个人扔给这对魔鬼,她会遭遇什么。
兰瑞想带妹妹走,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,只能敲门求助邻居。
最开始他只想知道怎么能带走妹妹,但为了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,他不得不一点点吐露出家里发生的这些事。
讲述这一段的时候,我第一次听到兰瑞抬高声音,流露出他被殴打、被安慰时都没有的激动神情。
他说家里突然来了很多人,有人情绪激动,说他们父母是混蛋,另一个人很快提醒他注意措辞,他们说这里有孩子,不能说脏话。
兰瑞呆呆地问他,为什么要道歉,说脏话原来是不对的吗?
有个女人告诉兰瑞,他得去法庭,这样就能让这对魔鬼彻底离开他的生活,还能得到他应得的保护和照顾。
“法院的大厅是大理石地面,有很多人急匆匆走过,鞋子嗒嗒地响,我看到一群人进了数字标记是1的法庭,我们的法庭门口是3,拉着禁止入内的牌子。”
“进入法庭,地面就变成地毯,我和兰琦全程只需要坐在最前面的椅子上。带我们来的人们走来走去,准备很多材料,法官坐得很高,他俯瞰整个法庭。”
“我看到了父母,他们站在被告席,一直负责我们的女人站在我们的斜前方,我觉得她在瞪着他们。”
“他们说的很多话我听不懂,兰琦抓着我的手,我们都低着头,怕被父母看见。”
那个晚上,兰瑞第一次和妹妹两个人睡在空空荡荡的大房子里,周围好安静,没有打砸东西的声音,也没有醉酒的人的鼾声。
兰瑞在房子里走了一圈,打开冰箱,拿出牛奶和冰淇淋。打开灯,拉出椅子,开始吃东西。
最开始他习惯性地轻手轻脚,接着他想起来,那两个会被吵醒然后大发雷霆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。
他把家里所有的酒全部倒进下水道,把瓶子装进大塑料袋,连夜拖到最近的超市门口,他只想这些东西快点消失。

这种无法控制的愤怒第一次出现,是在他想送妹妹兰琦去上学的时候。
为了帮从来没读过书妹妹办手续,兰瑞找了很多学校。这些学校没什么不好,只是因为离他们家近,多少都听过他们的事。
有个学校负责人同情地问,兰琦在家……是不是遭遇了很多痛苦的事?
负责人因此找了社工,说兰瑞很可能受父母影响,过于易怒,不适合再照顾兰琦。
而兰瑞则说,他只是不希望父母带来的伤害以“被人同情和关注”的形式,继续活在妹妹身上。
社工站在了兰瑞这边,并且建议他带着妹妹换个环境生活,也许一切就会好起来。
兰瑞带着兰琦搬了家,之所以选择维多利亚州,是因为这里有禁止家暴前科者入境的法规。
最开始他们住在政府提供的福利房里,有很多邻居,不时会出现有人走错门的情况,他们发现钥匙打不开门,会下意识地推两下。
兰瑞第一次被砸门声吵醒的时候,下意识从床上弹起来,抓起兰琦就把她往床底下塞。
兰琦惊恐地抓着他的胳膊大喊:“没事的!是邻居!是邻居!”
他讨厌同事说话、大笑的声音,干脆买了降噪耳机,全天戴着,有人和他说话就摘下来。
他的工作是公交司机,在选路线的时候,他主动提出要负责最偏远的那些。
负责人夸他年纪虽小但很敢承担责任,只有兰瑞自己知道,他是为了这些路线没人上车,清净。
他有一台特制的入耳式耳机,能把声音变成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感觉,不耽误工作,也不会吓到他。
公交公司规定开车时不能听音乐,兰瑞因此被警告过好几次,公司甚至说再这样就给他降薪。
这东西我知道,之前上过新闻,因为它有可能掉进耳道里拿不出来,让人变成聋子。
他既想上班挣钱养活自己和妹妹,又不敢面对自己对声音的恐惧,不敢面对那个地狱一样的童年。

兰瑞在一个晚上被妹妹叫醒,她半蹲在自己的床头,手里拿着一块毛巾。
兰瑞完全不记得自己是否做了梦,但他确实满身大汗,枕头和被子都丢在地上。
他问妹妹发生了什么,妹妹说,她被他的尖叫声吵醒了,听到他在喊“安静”,还不断砸墙。
他本想找之前的社工求助,但突然想起了学校负责人的那次举报。如果被发现精神不稳定,妹妹会被带走吗?
他想保持正常、假装正常,只有这样才能不和妹妹分开。
兰瑞给门做了隔音,加厚了窗户,房间里铺了厚厚的地毯。他想尽办法避免自己受到声音的刺激。
但同时,兰琦显然也很担心她的哥哥。每天晚上,她都会睡在哥哥的门口,一只耳朵贴在门上,怕他再做噩梦惊醒。
兰瑞怎么劝她也不回去睡觉,最后他干脆威胁她说,我就是因为你坐在门口才睡不好的,你回房间我才能休息好。
但是她也不再说话。她不会在兰瑞敲门时欢天喜地地大喊“我来了”,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唠叨要哥哥好好吃饭。
比如,把碗筷摆在桌上,指一指饭碗,就是问哥哥有没有吃主食,指一指盘子,就是提醒他要吃蔬菜。
每天晚上,她还是会来和兰瑞道晚安,她会看着他躺下,然后用手压在他眼睛上,就像父母在那间房子里砸东西的时候她捂住他的耳朵。
在一个半梦半醒的时刻,兰瑞听到妹妹发出轻轻的叹息。
他觉得妹妹最近好像不爱说话,但没有意识那是几天来,他唯一一次听到兰琦的声音。
从不说话,蹑手蹑脚,到根本不再有动作,只会悄悄地坐在哥哥身边,像一个安静脆弱的洋娃娃。
兰瑞是她的病根,但这不是因为他伤害了她,而是因为她想保护他。
我继续向他解释:“兰琦不应该去精神病院,实际上应该去医院的是你。你知道你再发展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吗?”
兰瑞经受过严重的家庭暴力,没有走出来,这并不奇怪。
但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,他会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,他会从喜欢安静,到习惯安静,到受不了不安静。
就像他对刷视频的我发火一样,他可能会对兰琦发火,可能会打她,他可能会要求她保持安静,最后可能会希望她绝对的安静——
那就是死亡,让她彻底变成一个洋娃娃,摆在他身边,陪着他。
他可以试着自己阻止这一切,但兰琦呢?兰琦又会做什么,来“保护”哥哥?
兰瑞站起来抓着我,甚至有些发抖。他说我们马上去医院。
我们都知道,等待着他的可能是三年左右的治疗,他还可能被剥夺对妹妹的抚养权。
我其实已经做好准备,兰瑞会把我视为要夺走妹妹的敌人,甚至对我动手。毕竟他在那样的家庭长大,而且一直把妹妹视为救命稻草。
他在乎妹妹的未来,比任何人都更在乎。他还没有变成他父母那样的人。
我给这对兄妹一块办了入院申请,我护送兰琦,另一个护士领着兰瑞。
我没有去听他们在说什么,但回来的时候兰瑞并没有哭,看起来很平静。
而兰琦还处于“洋娃娃”的状态,乖乖地牵在我手里,一步步走进了自己的病房。
这里很安静,但又不像兰家那么安静,有鸟叫的声音,有孩子们的笑闹。
就像之前几次治疗一样,过不了多久,兰琦就会恢复正常,融入这片笑声中。

在这个故事里,表面生病的是兰琦,但真正生病的是兰瑞。
他从小是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,但也耳濡目染被黑暗侵染,连最关心他的兰琦也受到影响。
侯小圣这么跟我评价的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:
“这是一对习惯等待和煎熬的兄妹,但现在,兰琦的等待不再是一种煎熬了。这是一种真正的盼望。”
这也是最打动我的一部分。
从出生起,我们无时无刻不受到父母影响,带着原生家庭和他人见面。
但与那些选择伤害孩子的父母不一样,我们在深知被什么伤害后,会为了那些爱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,慢慢变好。
(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)
编辑:卡西尼 小旋风
本文收录于合集: